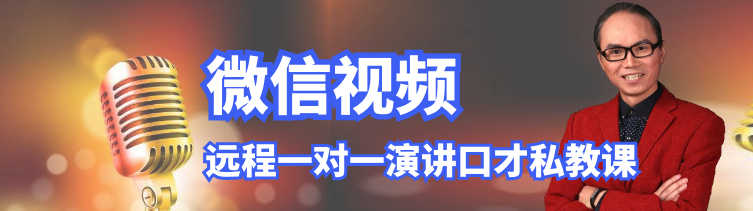Star055 顿悟,改变只在刹那间

文/恰恰天蓝
1
说来我国的太极(阴阳)文化总是时不是给我们以启示,让人很轻易的可将任意的事物“一分为二”来观察和评判,似乎这成了国人的本能。
我成长的经历中,有两件小事对我启发很大,曾也多次在我的习作中提到,就是我是怎么样很快(快差不多是自学)掌握游泳和骑自行车的技能的,这里有一个两者相通的关键点,就是感觉(get)到了“平衡”,只要把握住了这个点,憋一口气在水中体验到自己的“悬浮”,或从有一定斜度的坡上单脚溜下来感受自由掌控方向的乐趣,每到这样的时刻,我知道我已经学会了这项技能,后面是变着花样怎么去反复练习熟能生巧了。刹那间,我感受到了“学会”的另一个世界的不一样,这是不是所谓的顿悟学习的一种呢?
还有一件事情是,我是怎样体会到“人是怎样突然之间长大的了”,具体事情不记得了,时间发生在我读初高中的时候,有一次,周末回家,母亲问我一件事情(大概是关于外婆家那边的事)怎么处理才好,她在征求我的意见哟,突然之间我就感觉全身像触电一样,一下就换了个人似的,因为在这之前我觉得诸如这样的事情都听大人的决定就好了,而那一刻,我看着母亲茫然的眼神,真切地感受到了母亲无助的渴望,刹那间,我似乎明白了一切,这个家的担子正在发生交接。用现在的眼光来看,从此,家里很多事情需要我自己做决定,并承担后果了。
2
李笑来老师在《人人都能用英语》的开章也讲到了这个“顿悟”时刻,很是精彩,我根本不想删改一丁点,读者诸君于是更能体会这种微妙的“刹那间”,他说:
有另外一种知识,往往还是格外重要的知识,在知道它的那一瞬间就可能开始发挥重大的作用,甚至,在知道它(What)的那一瞬间,它所有的重大作用全部都发挥完毕(至于Why和How,甚至可能在了解它的What那一瞬间早已经不言自明)。在我个人的记忆里,一路上遇到过很多这种“只要知道就能够瞬间全部发挥作用”的知识。学概率统计的时候,遇到“独立事件”这个概念,就是这类知识的典型例子。在此之前,我很自然地以为如果连续9次抛硬币都是正面朝上,那么第10次抛出硬币之后正面朝上的可能性要远远低于背面朝上的可能性……在概率教科书里读到“独立事件”的那一瞬间,让我意识到之前的想法是多么的可笑。因为抛硬币正反面的几率是永远都相同的(硬币出现正反面在每次抛时都是相互独立、不受之前结果影响的),各占50%,所以即便我抛一百次,一万次,甚至更多次都是正面朝上,下一次抛正反面的几率也还是如此,各占50%。至此,这个知识的所有作用已经全部发挥完毕:它能够彻头彻尾地改变一些人——那些一不小心看到它实际意义的人。无论是谁,在做几乎所有决定的时候,都要考虑“可能性”(学称“概率”)。在我不知道“独立事件”这个概念之前所做出的很多决定,换在知道“独立事件”这个概念之后,我是无论如何都不会那样选择的——这就是改变,并且是质变。
注意,从笑来老师这次“概率”顿悟事件中,你“get”到几个关键点呢?
第一个,这是一种往往格外重要的知识;
第二个,一门学科(概率学)其实就是明白一个核心概念(“独立事件”);
第三个,瞬间发生,切断过往,导致质变;
……
3
这不由得让我想起,被毛主席誉为中国佛教始祖——“禅宗六祖”的惠能大师顿的故事,这座位于韶关曲江曹溪的“南华寺”我去过两次,开始是带着强大的好奇心去瞻仰“六祖真身”的,后来了解到有关慧能顿悟成佛的那些事迹,特别是那首偈叫人印象深刻,过目不忘:
菩提本无树,明镜亦非台。本来无一物,何处惹尘埃。
记得那时,读到这首偈后,让我等非佛中人,即刻既有了然佛法的爽感,此前那些困扰我的世界性问题,刹那间,释然。哪里有什么道佛神仙,哪有什么妖魔鬼怪, 一切皆心性。
真是心性自在,佛陀的顿悟,就是一念一世界。
还有一例,是明朝时的王守仁“龙场悟道”的故事,他创建的“知行合一”的“阳明心学”对后世影响极大,比如曾国藩,还有日本。
4
查“顿悟”一词,意为自发地对某种情境中各刺激间的关系的豁然领会。
上周始开始主动接触“心理学”,原来我认为的“我”不是真的“我”,所谓的“我”很可能是两个或是三个我组成的,而那个潜意识的我,以及驾驭马车的人的我,使我的认识不觉间又上升了一个档次,而我之前因“愚昧”一直排斥,错过二十年。
于是,我又在网上搜索有关“顿悟”科学方面的一些东西,发现了一个叫“格式塔学习理论”的方法论,且曾经很流行,它的一个观点是:人和动物都是靠顿悟来学习的,这个过程是不需要依赖于练习或经验的。但一定的经验积累,是产生顿悟的前提。
还有一个“物理现象和生理现象也有完形的性质”让我很是好奇。
原来我还差得远呢。
但我明白,Get到那个点,就能顿悟。
- AI并不能让我们告别写作焦虑:掌握“元写作”,让表达清晰有力
- 老鼠与船夫的矛盾,究竟该如何化解?
- 跨越肤色的联结:美国白人黑人通婚家庭的现状、动因与挑战
- 海南全岛封关运作:高水平开放的里程碑与生活新图景
- 告别灵感依赖:用“元写作”重塑你的文字表达力
- 对话“荣昌老高”:泼天流量当然要接住,“卤鹅哥”走红后看到了机会,我当时还有3个月满60岁,已做好交接准备
- 真正聪明懂事的孩子,不是教育出来的
- 多次应试才登第——历史上那些屡败屡战的名人们
- 十年前学了一次钻石法则,现在依然受用
- 对金刻羽来说,现在的危险不在绯闻,而在叙事
- 知名教授宾大演讲:我的讲稿是AI写的,但你们依然需要我
- 成功者顶级心法
- Token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发明
- 从众:跟随群体的心理惯性(底层逻辑022)
- 偏见:先入为主的判断倾向(底层逻辑021)
- 意义感:对存在价值的追求(底层逻辑020)
- 2025.11.16
- 樊荣强:如何通过钻石法则提升演讲自信?
- 十年验证:我的钻石法则,为何能让演讲口才受益终身?
- 《神经——元思维:问与答的思考及表达智慧》的创作背景解读
- 契诃夫名言
- 把清晨还给自己
- 与豆包AI对话:内阁这个词的含义以及出处
- 以写作为舟,渡思辨之海:基于樊荣强元写作理论的能力提升方法论
- 樊荣强:疑问句激活思路的心理学机制与实践分析
- 为何疑问句能激活思路?关于语言生成的心理学分析
- 职场第六课:想快速提升?抓住这三个关键就够了
- 十年前蹭的课,现在还受用——樊荣强的口才课到底好在哪儿?
- 职场第五课:不要说服对方,而要引导对方自己说服自己
- 石凳装扶手:揭秘为什么“一人生病,全家吃药”是必须的